胡同里的微型城市化
01 October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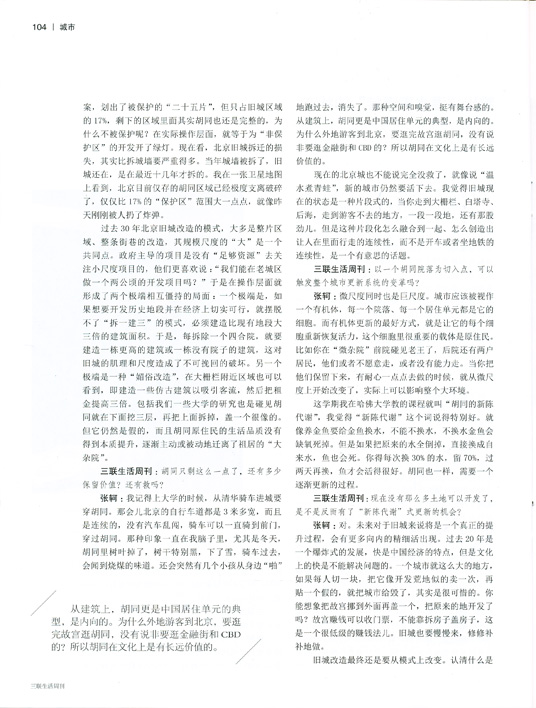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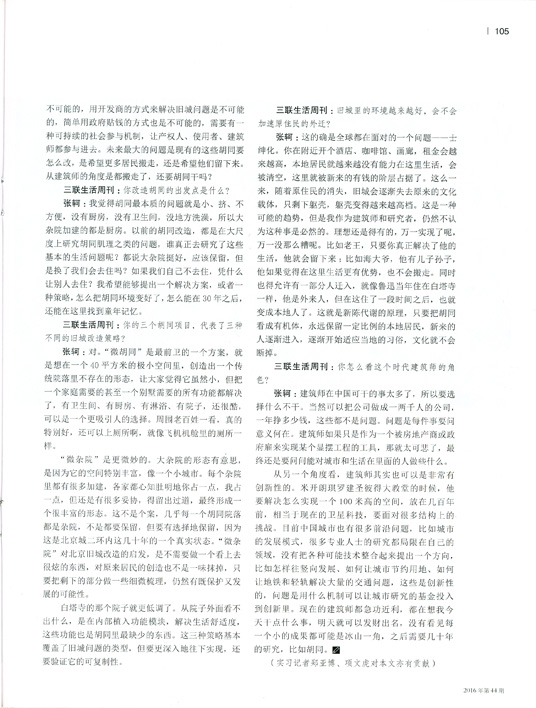
贾冬婷
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大奖中,普遍认为普利兹克奖是关注建筑前沿的,而源于伊斯兰世界的阿卡汗奖是偏重人文关怀的。但是,谁能说人文关怀不是建筑前沿呢?——这也是对新一届阿卡汗奖得主张轲的胡同改造实践的最好注解。
茶儿胡同8号院,王大爷正在院里忙活着什么。他身上的藏蓝色卡其布上衣还齐整,头发却很长时间没打理,一绺一绺地垂在谢了顶的脑袋周边,有些实在太长了,就干脆在头顶绕一个圈,颇有些仙风道骨的意思。
“我不搬走,东西太多,麻烦。”他说着话,从屋里拿出来几个塑料袋,把里面的零碎物件一个一个拿出来,在院子平台上摊开,重新分类,再心满意足地系上口。这是他的日常生活,也在无形中宣示着对这块地盘的所有权。他从小住在附近胡同,后来为了上班方便,和这院的一户人家换了房,搬过来已经30多年了。
王大爷是前院唯一的住户了。他的屋子朝南,占了正房三分之一的面积。院子里还有一间几十年前的加建,当作厨房和杂物间。属于他的这几间,一直顽强地保留着原貌,他不让动,因为只要墙的厚度改变一点,面积就可能差一平方米,损失就得几十万元。其余搬走的几户空出来的房子,被张轲重新改造了。有意思的是,外人很难一下子分清哪间是旧的,哪间是新的,因为院子的格局没变,外表看仍然是斑斑驳驳的灰砖,甚至大杂院里各家各户加建的厨房也都没拆。
“原来这里是座庙,所以比别的院子大,解放后住了十几户呢。”王大爷说。果然,门楣上还保留着“重修灵鹫寺”字样,咸丰年间重修的,据说原建于明朝。王大爷住的正房,原来是庙的正殿,房瓦和木架经过整修后,显出巍峨的气度。院里还放着一个圆柱形石墩,是原来观音像的底座。“‘文革’时‘破四旧’,观音像被砸了,就剩这个观音座了。”王大爷告诉我,它有镇宅作用,不能挪出这个院子。
占据院子中央的是一棵老国槐,高度早已超越了屋顶,枝叶繁茂,四向伸展,护荫着整个院落。这棵树是小院历史最长久的见证者。老人们说,庙还没建的时候,树就在了,如今是大栅栏地区五棵一级古木之一。即便在人口急剧增长的年代,十几户人家在院中间加建厨房,这棵树的地位也没有丝毫动摇。改造前,粗壮的树干被几家人的厨房包围着,它们在不同高度的枝丫下方,高高低低地错落排布。
2012年张轲受西城区政府邀请,在大栅栏区域选一个院子进行改造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棵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我进去的时候,一多半的人都搬走了,院子里污水横流。但是那棵老槐树太漂亮了,我觉得简直就是中国传统家庭的一个象征。”在张轲眼里,这棵树为院子增添了不少灵气,而且还带来一种文化隐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不约而同地将“槐树”与知识、学习联系在一起。建筑大师路易斯˙康曾说“第一所学校始于一棵大树下”,孔子更是在槐树下授课讲道。原来绕树而建的几间小厨房,错落堆积地像是几级台阶,张轲索性就改建成一个锯齿状的不规则空间,外墙也是台阶,可以上到一个平台,高度在屋顶之上,树冠之下,周围是起伏的灰色屋顶。平台上用粉笔涂满了五颜六色的格子,显然已经被胡同里的孩子们占领。
就像“微杂院”这个名字所传达的,张轲介入改造的方式很微妙。他认为,之前的改造,不管是保护还是开发,第一件事都是把加建部分先删除,而“微杂院”是先把它们保留,然后有一些修复,有一些改建。在他看来,它们正是同院居民互相博弈和妥协的产物,最终的结果是在不大的边界范围内,构成了微尺度的街巷空间和丰富的社交网络。材料上也尽量不着痕迹,选用了北京本地回收的旧砖和一种“墨汁混凝土”。这种混凝土是张轲发明的,顾名思义就是在混凝土里加入墨汁,让颜色更灰暗,再采用和砖同样宽度的模具,在视觉上就和灰砖非常接近,带来一种新旧融合的效果。
因为不远处就有一所炭儿胡同小学,张轲将改造后的“微杂院”定位为一个儿童活动空间。旧的空间和肌理没有显著改变,但是每一个空间里的功能变了:绕树的几个加建厨房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型艺术展厅;南房剩余空间被设计为一个舞蹈教室;东厢房的坡屋顶下安插了一个儿童图书室,开了全景窗,加宽的窗台模仿了台阶的形式,可以当作阅读时的座椅和书桌,也可以爬坐到窗台上看外面的院子。
住在斜对面茶儿胡同9号院的海大爷拿着一串钥匙走进来,他是“微杂院”的兼职管理员。他更关心胡同里的生活需求,听说张轲之后还想搬进院子一个集成卫生间、厨房、洗衣机等的功能模块,有些不同意见。“关键是厨房弄利落了,卫生间倒是无所谓。现在住胡同里,用不了两分钟就能走到公共厕所,挺好。要在院里搞,一个院子总有好几户,厕所不可能一户弄一个。只有一个的话,将来卫生谁搞?就会制造矛盾。”当然茶儿胡同改造已经带来不少变化。“胡同里过去都没人扫,把垃圾‘噗’地往门口一扔,就不管了。现在打扫干净了,有了垃圾桶,他即便要扔,也得琢磨琢磨,不可能满大街扔。是这个道理吧?”他悄悄跟我说,王大爷之前那件衣服都穿得像油毡一样了,院子里来的孩子和游客越来越多,他不也换了件干净的?
在张轲看来,留在胡同里的居民大致有三种:一种是王大爷这样的,没有能力搬走。他单身,只有这一处十几平方米的房子,能拿到的补偿也就200多万元,这些钱他能买到什么?能在市中心生活方便的地方买一套房子吗?还有一种是像海大爷这样的,他是回民,在9号院有三间房,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四代,离不开了。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和老两口住,儿子在顺义上班,从这边坐公交和地铁更方便,而5岁的孙子在牛街上幼儿园,在骑车半小时以内的距离。如果搬走,给两个儿子一人一套房,就得搬到五环外,比住在这差远了,不方便,还贵。还有第三种人,租住在胡同里,做点小买卖,他的孩子可能也在这附近上学。张轲说,他在“微杂院”中试图实现的目标就是共生,不仅是空间上的共生——城市过去和现在的共生;原有主体建筑和居民自发加建的共生;院落中新功能和原有居住功能的共生,更是不同人群之间的共生——院内居民和周边居民、社区居民和外来参观者的共生。
为了居民之间的“共生”,张轲找到居委会帮忙,还争取到社区内一个建于明朝的清真寺的支持,海大爷就是清真寺的阿訇推荐来做管理员的。海大爷告诉我:“附近有琉璃厂,那是过去为盖皇宫烧琉璃瓦的。我以前工作的饭馆就在西琉璃厂,挖防空洞时挖到一米多深,发现都是碎琉璃瓦。这条胡同原来叫‘柴胡同’,就是为烧琉璃瓦存柴火的地方,民国时才叫成‘茶儿胡同’了。”他说,前门大街东侧一整片全拆了。西侧大栅栏地区启动晚,不让拆了,才保留了。“再拆,北京城就没了。”
海大爷告诉我,这些大杂院里的加建,也有40多年了。“最早的四合院里,厨房卧室带茅房全在一间屋里。夏天就在窗台上支个锅,冬天在屋里做饭。这种单独的厨房从什么时候兴起的呢?是因为唐山大地震,开始搭地震棚,后来变成厨房。家家都盖厨房,你也弄一间,我也弄一间,就这么起来的。”在张轲眼里,这些加建也已经变成了当代城市历史的一部分。“胡同最吸引人的是每户居民都进行了更改,以适应他的生活方式。如果要把它直接恢复到100年前,那也是假的。你能想象在罗马去拆毁一座美丽的建筑,只因为它在几百年前未被授权吗?它存在了,就有它的价值,不应该是简单地抹掉以后再美化。”
关于微杂院日后的使用,张轲曾在社区里做过调查,很多人都说想让孩子学英语。他觉得,那太简单了,很多志愿者就可以教。但真正运营起来却没那么简单。比如费用,有人建议在利用场地进行教学的时候,对参加者收取很低的费用,把老师的课时费抵消掉,可是张轲比较理想化,不想对居民和场地收取一分钱。不过海大爷5岁的小孙子已经在这里玩得不亦乐乎了,他自称“队长”,会跟小朋友们说,进这边要脱鞋,进那边要关门,书看完要放回去。胡同里的孩子们也都下意识地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地方了。
茶儿胡同8号的“微杂院”是张轲在胡同里的第二次实践。在此之前,他还在杨梅竹斜街上做了”微胡同”项目,是把两个大的杂院分成七个窄条的院子,分别进行整理。在其中的一个院子里,他将40平方米的老房子改造成一个被五个房间交错围绕的庭院,试图从内部生长出异质的新空间,给新来的人使用。相比较而言,微杂院是更微妙的,是对一些原来居民创造的东西进行细微的改造,跟居民共生。之后又在白塔寺区域的宫门口四条36号改造了一个院子,在内部加入一个极小化的卫生间、淋浴、厨房等的集成模块,解决的是每一个细胞的问题。
“‘微杂院’入选,是因为它体现了传统北京胡同院落里的现代生活。”本届阿卡汗建筑奖(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组委会指出。这一奖项由阿卡汗四世于1977年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旨在”肯定并鼓励那些成功诠释穆斯林社会的需求与期许的建筑概念”,尤其在这个西方文明以现代化的名义席卷全世界的年代,期望建筑师从解决实质问题出发,协调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平衡,实现对本地区建成环境的保护和创造。对“微杂院”的评语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标准:“微杂院为老建筑的重新利用提供了一条参考道路,甚至可以为容纳创意内容、提供公共或私人交替使用功能的微型城市化,创建一种新型模式。”
跳出”温水煮青蛙”的状态
——对话标准营造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张轲
我是在北京二环路和三环路之间的标准营造事务所见到张轲的。这个位置处在旧城和新城的交界地带,离他所做的几个胡同项目也都不远,他常常沿着二环路坐上地铁,再走几步路,就到了胡同。他的这间事务所也像是在胡同文化里长出来的——灰砖包裹的三面长条形建筑围合成一个庭院,站在会议室长达12米的大玻璃窗前,可以看见整个庭院。院子里种了30多棵树,都是张轲自己选的,他说:“现在还是树叶基本都绿的时候。你看那棵白蜡昨天开始变黄了,可能再过一周,所有的白蜡都会变成黄的,再过两周,所有的枫树就全变红了。之后会持续一周,灰砖地面上这边一地红叶,那边一地银杏叶。这种季节变化的存在感,是可以通过植物的形态和气味变化强化出来的,这也可以部分地说明胡同在今天存在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微杂院”不太像是一个传统的建筑项目,而更像是以胡同为切入点,探讨北京旧城改造的新的可能性。你对这方面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轲:最早是在清华大学时的硕士论文,我写了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Charles Correa),他的研究是从城市设计角度,怎么为穷人做设计。他用一种草根的视角去看城市,其中有一项对孟买的研究,我现在还记得挺清楚,就是孟买有些人有工作,但是没有房子住怎么办,这在贫富差距严重的印度是很真实的问题。查尔斯˙柯里亚在人行道边上做了一个台子,让没有房子的白领晚上睡在这里,第二天早上又可以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去上班。一定程度上,他唤起了我作为一个建筑师对社会的清醒看法,开始对城市发展模式感兴趣。我在论文里提到一个“温水煮青蛙”的隐喻,就是我们的城市可能就像温水里的青蛙似的,会有一种慢慢加热,慢慢毁灭的过程。它不像战争时期被炸弹炸毁了那种强烈的感受,而是在你觉得越来越轻快、越来越舒服的同时,文化被毁掉了。当意识到想要跳出来的时候,已经被煮得瘫软,跳不出来了。
当然这是一个挺悲观的故事。等我2001年赢了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的国际竞赛,决定从美国回到中国之后,想法就有些变了。我觉得,这个状况可能很糟糕,但它不可能更糟糕了,只可能变得更好,所以建筑师是可以做点事的。
三联生活周刊:“温水煮青蛙”的隐喻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实的?
张轲:我写那篇论文是在90年代中期,其实当时没想到旧城的破坏会那么严重,胡同里的大拆大建是在2000年以后。当时有一个历史文化区域保护方案,划出了被保护的“二十五片”,但只占旧城区域的17%,剩下的区域里面其实胡同也还是完整的,为什么不被保护呢?在实际操作层面,就等于为“非保护区”的开发开了绿灯。现在看,北京旧城拆迁的损失,其实比拆城墙要严重得多。当年城墙被拆了,旧城还在,是在最近十几年才拆的。我在一张卫星地图上看到,北京目前仅存的胡同区域已经极度支离破碎了,仅仅比17%的“保护区”范围大一点点,就像昨天刚刚被人扔了炸弹。
过去30年北京旧城改造的模式,大多是整片区域、整条街巷的改造,其规模尺度的“大”是一个共同点。政府主导的项目是没有“足够资源”去关注小尺度项目的,他们更喜欢说:“我们能在老城区做一个两公顷的开发项目吗?”于是在操作层面就形成了两个极端相互僵持的局面:一个极端是,如果想要开发历史地段并在经济上切实可行,就摆脱不了“拆一建三”的模式,必须建造比现有地段大三倍的建筑面积。于是,每拆除一个四合院,就要建造一栋更高的建筑或一栋没有院子的建筑,这对旧城的肌理和尺度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另一个极端是一种“媚俗改造”,在大栅栏附近区域也可以看到,即建造一些仿古建筑以吸引客流,然后把租金提高三倍。包括我们一些大学的研究也是碰见胡同就在下面挖三层,再把上面拆掉,盖一个很像的。但它仍然是假的,而且胡同原住民的生活品质没有得到本质提升,逐渐主动或被动地迁离了祖居的“大杂院”。
三联生活周刊:胡同只剩这么一点了,还有多少保留价值?还有救吗?
张轲: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从清华骑车进城要穿胡同。那会儿北京的自行车道都是3米多宽,而且是连续的,没有汽车乱闯,骑车可以一直骑到前门,穿过胡同。那种印象一直在我脑子里,尤其是冬天,胡同里树叶掉了,树干特别黑,下了雪,骑车过去,会闻到烧煤的味道。还会突然有几个小孩从身边“啪”地跑过去,消失了。那种空间和嗅觉,挺有舞台感的。从建筑上,胡同更是中国居住单元的典型,是内向的。为什么外地游客到北京,要逛完故宫逛胡同,没有说非要逛金融街和CBD的?所以胡同在文化上是有长远价值的。
现在的北京城也不能说完全没救了,就像说“温水煮青蛙”,新的城市仍然要活下去。我觉得旧城现在的状态是一种片段式的,当你走到大栅栏、白塔寺、后海,走到游客不去的地方,一段一段地,还有那股劲儿。但是这种片段化怎么融合到一起、怎么创造出让人在里面行走的连续性,而不是开车或者坐地铁的连续性,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三联生活周刊:以一个胡同院落为切入点,可以触发整个城市更新系统的变革吗?
张轲:微尺度同时也是巨尺度。城市应该被视作一个有机体,每一个院落、每一个居住单元都是它的细胞。而有机体更新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它的每个细胞重新恢复活力,这个细胞里很重要的载体是原住民。比如你在“微杂院”前院碰见老王了,后院还有两户居民,他们或者不愿意走,或者没有能力走。当你把他们保留下来,有耐心一点点去做的时候,就从微尺度上开始改变了,实际上可以影响整个大环境。
这学期我在哈佛大学教的课程就叫“胡同的新陈代谢”,我觉得“新陈代谢”这个词说得特别好。就像养金鱼要给金鱼换水,不能不换水,不换水金鱼会缺氧死掉。但是如果把原来的水全倒掉,直接换成自来水,鱼也会死。你得每次换30%的水,留70%,过两天再换,鱼才会活得很好。胡同也一样,需要一个逐渐更新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没有那么多土地可以开发了,是不是反而有了“新陈代谢”式更新的机会?
张轲:对。未来对于旧城来说将是一个真正的提升过程,会有更多向内的精细活出现。过去20年是一个爆炸式的发展,快是中国经济的特点,但是文化上的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个城市就这么大的地方,如果每人切一块,把它像开发荒地似的卖一次,再贴一个假的,就把城市给毁了,其实是很可惜的。你能想象把故宫挪到外面再盖一个,把原来的地开发了吗?故宫赚钱可以收门票,不能靠拆房子盖房子,这是一个很低级的赚钱法儿。旧城也要慢慢来,修修补补地做。
旧城改造最终还是要从模式上改变。认清什么是不可能的,用开发商的方式来解决旧城问题是不可能的,简单用政府贴钱的方式也是不可能的,需要有一种可持续的社会参与机制,让产权人、使用者、建筑师都参与进去。未来最大的问题是现有的这些胡同要怎么改,是希望更多居民搬走,还是希望他们留下来。从建筑师的角度是都搬走了,还要胡同干吗?
三联生活周刊:你改造胡同的出发点是什么?
张轲:我觉得胡同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小、挤、不方便,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没地方洗澡,所以大杂院加建的都是厨房。以前的胡同改造,都是在大尺度上研究胡同肌理之类的问题,谁真正去研究了这些基本的生活问题呢?都说大杂院挺好,应该保留,但是换了我们会去住吗?如果我们自己不去住,凭什么让别人去住?我希望能够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或者一种策略,怎么把胡同环境变好了,怎么能在30年之后,还能在这里找到童年记忆。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三个胡同项目,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旧城改造策略?
张轲:对。“微胡同”是最前卫的一个方案,就是想在一个40平方米的极小空间里,创造出一个传统院落里不存在的形态,让大家觉得它虽然小,但把一个家庭需要的甚至一个别墅需要的所有功能都解决了,有卫生间、有厨房、有淋浴、有院子,还很酷,可以是一个更吸引人的选择。周围老百姓一看,真的特别好,还可以上厕所啊,就像飞机机舱里的厕所一样。
“微杂院”是更微妙的。大杂院的形态有意思,是因为它的空间特别丰富,像一个小城市。每个杂院里都有很多加建,各家都心知肚明地你占一点,我占一点,但还是有很多妥协,得留出过道,最终形成一个很丰富的形态。这不是个案,几乎每一个胡同院落都是杂院,不是都要保留,但要有选择地保留,因为这是北京城二环内这几十年的一个真实状态。“微杂院”对北京旧城改造的启发,是不需要做一个看上去很炫的东西,对原来居民的创造也不是一味抹掉,只要把剩下的部分做一些细微梳理,仍然有既保护又发展的可能性。
白塔寺的那个院子就更低调了。从院子外面看不出什么,是在内部植入功能模块,解决生活舒适度,这些功能也是胡同里最缺少的东西。这三种策略基本覆盖了旧城问题的类型,但要更深入地往下实现,还要验证它的可复制性。
三联生活周刊:旧城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会不会加速原住民的外迁?
张轲:这的确是全球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士绅化。你在附近开个酒店、咖啡馆、画廊,租金会越来越高,本地居民就越来越没有能力在这里生活,会被清空,这里就被新来的有钱的阶层占据了。这么一来,随着原住民的消失,旧城会逐渐失去原来的文化载体,只剩下躯壳,躯壳变得越来越高档。这是一种可能的趋势,但是我作为建筑师和研究者,仍然不认为这种事是必然的。理想还是得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万一没那么糟呢。比如老王,只要你真正解决了他的生活,他就会留下来;比如海大爷,他有儿子孙子,他如果觉得在这里生活更有优势,也不会搬走。同时也得允许有一部分人迁入,就像鲁迅当年住在白塔寺一样,他是外来人,但在这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变成本地人了。这就是新陈代谢的原理,只要把胡同看成有机体,永远保留一定比例的本地居民,新来的人逐渐进入,逐渐开始适应当地的习俗,文化就不会断掉。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这个时代建筑师的角色?
张轲:建筑师在中国可干的事太多了,所以要选择什么不干。当然可以把公司做成一两千人的公司,一年挣多少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每件事要问意义何在。建筑师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被房地产商或政府雇来实现某个显摆工程的工具,那就太可悲了,最终还是要问问能对城市和生活在里面的人做些什么。
从另一个角度看,建筑师其实也可以是非常有创新性的。米开朗琪罗建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他要解决怎么实现一个100米高的空间,放在几百年前,相当于现在的卫星科技,要面对很多结构上的挑战。目前中国城市也有很多前沿问题,比如城市的发展模式,很多专业人士的研究都局限在自己的领域,没有把各种可能技术整合起来提出一个方向,比如怎样往竖向发展、如何让城市节约用地、如何让地铁和轻轨解决大量的交通问题,这些是创新性的,问题是用什么机制可以让城市研究的基金投入到创新里。现在的建筑师都急功近利,都在想我今天干点什么事,明天就可以发财出名,没有看见每一个小的成果都可能是冰山一角,之后需要几十年的研究,比如胡同。